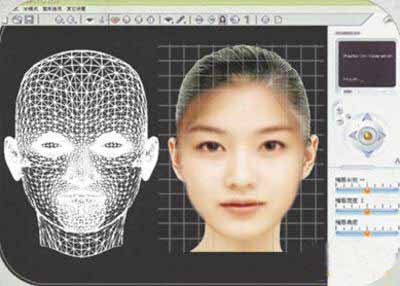���A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ɺ�c�m(x��)��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
����D����ˮ�ھ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Ԭ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�ʩ�����`��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ԭ�����C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ɺ�������14�q��܊���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Б�(zh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һ�����·�Ԭ����(zh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½��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li��n)�j(lu��)ͬ־���e�x������1914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ɺ���Aɽ�r(sh��)�Y(ji��)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ͬ�˕�(hu��)�T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Ҋ(ji��n)��ʣ���ͬ���Aɽ�_��҈@�ĸ����h�˹�ϣ�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?c��)ڗ�҈@����ȪԺ�����v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li��n)�j(lu��)���ظ����h�˿vՓ���´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һ�r(sh��)�g���Aɽ֮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�H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صĸ����h�˼���?d��ng)����?l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m(x��)��ͤ���ؑ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£��m(x��)ͩϪ�����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ɺ�������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·��m(x��)��ͤ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ɽ��֮��҈@��Ӌ(j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(li��n)�j(lu��)�ᴨ��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ϵ֮�ϳ����Ї�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횴���ϵ���ܳɹ����Դ˞�Ŀ��(bi��o)������ҷ��^�M(j��n)�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Կ��^�Aɽ���x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A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l(f��)�M(j��n)�е�һ�θ���(li��n)�j(lu��)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Ҳ��һ�����Y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܊�������ľە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mȻ�](m��i)���ƶ����w�Є�(d��ng)�V�I(l��ng)��Ӌ(j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|(zh��)���γ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܊�¼��F(t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г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hu��)ͬȫ��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h�˞��Ʒ�Ԭ���P����(q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܊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Ļ���Ŀ��(bi��o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l��i)����Aɽ���x�Ĵ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ɆT�������ɞ��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܊����Ҫ�M�ɲ��֡������܊�Ĺ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ɺ���m(x��)��ͤ�Ǿ��x־ʿ�����g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˽Y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飬����ɺ��(du��)�L(zh��ng)�Լ�һ�q���m(x��)��ͤʼ�K�����L(zh��ng)��֮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1918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ɺ�S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ԭ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gu��)܊���x�죬�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˾�����1923������ɺ������핺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һ�ÈF(tu��n)�L(zh��ng)���m(x��)��ͤ�������΅��\�L(zh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ӑ�����ڵđ�(zh��n)��(zh��ng)���1927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)�·�(gu��)��(li��n)܊܊�����ΌW(xu��)УУ�L(zh��ng)���m(x��)��ͤ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δ�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r(sh��)�·�(gu��)��(li��n)܊�vꃿ�˾�����˾�������ɺ�ͷ��ˏ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ͽ�B�m(x��)��ͤ�c�S��zϲ�Y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@һ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ɺ��D߀�����ٳ��ˮ�(d��ng)�r(sh��)�·�(gu��)��(li��n)܊�����β��L(zh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(ch��n)�h�˄�����(ji��n)�c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

�������š�һ�ˡ���׃���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ɺ�����m(x��)��ͤ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\�L(zh��ng)��1934���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ɺ�����܊�¾���һ܊܊�L(zh��ng)����һ܊���\�L(zh��ng)һ���Ͼ��Ɇ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(x��)��ͤ������һ܊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˕r(sh��)�ۇ�(gu��)���x��ռ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߄��A����׃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gu��)���h��(d��ng)��(du��)��ҕ����Ҋ(ji��n)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ˡ��t܊�������و�(ch��ng)�A܈�����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@Щ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ʹ�m(x��)��ͤ��Бn�]�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̡�

����1935��11��15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(x��)��ͤ��(l��i)���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(k��i)����Ç�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hu��)֮�C(j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վȇ�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(gu��)����(hu��)�](m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κΛQ�h���Ҋ(ji��n)���ăH�H���Y��ʯ���P(gu��n)���⽻���h���еĎ�Ԓ������ƽδ����ȫ�^���ĕ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Q���ŗ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δ�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Q���p�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(x��)��ͤ��ϣ���ص��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b��o)��(gu��)�o(w��)�T(m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܊�ˣ�Ո(q��ng)�t�o(w��)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ʧ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ŭ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12��26������4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Ͼ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ް�����ɽ��֮���Զ̄��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(y��)Ժ�þȡ�
�����@Ϥ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ɺ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늽o�m(x��)��ͤ�����@Ϥ���֑n��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Դ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(sh��)�X(j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500Ԫ����ˎ�M(f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b��o)��(gu��)֮�շ��L(zh��ng)����ϣ���^�o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늷�ο�������1936��2�³����m(x��)��ͤ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՝u���D(zh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ɺ?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鰲�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ص��ɼ��˲��y��ǵ������т�?y��u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(y��ng)�I��Ŀ��(xi��ng)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s���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ɺһ���˵ĵ���(l��i)���m(x��)��ͤ�dz�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H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

����1938��5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·�^(gu��)�Ӱ��r(sh��)��δ��֪�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Ӱ����P(gu��n)һ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Ӱ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)�ψ�(b��o)�������ë�ɖ|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ָʾ߅�^(q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H̎һ��Ҫ���Қgӭ��¡�ؽӴ�����߅�^(q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H̎�L(zh��ng)��Ǯ�(d��ng)ҹ�s����R�꣬Ո(q��ng)����һ�а���߅�^(q��)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ց�(l��i)��Ҋ(ji��n)����ɺ���D(zhu��n)�_(d��)��ë�ɖ|��ꃸʌ�߅�^(q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ʢ���y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ס��(l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ë�ɖ|ͬ��·܊���ر��F(tu��n)˾��TФ�Ź��H��(l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Ո(q��ng)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ˆ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Ф�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ë�����\(ch��ng)���Є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Ӱ���ס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˿������ꃱ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ȣ���ϯ�˚gӭ���(hu��)��Ⱥ���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�Ҋ(j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ꃱ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W(xu��)��(x��)�Ķ�Ů������÷����Y(ji��)�R(sh��)ë�ɖ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ߵĵ�·�a(ch��n)���˘O��Ӱ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ɺ�c�m(x��)��ͤ�ٴ���Ҋ(j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943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6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ɺ���(gu��)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ؑc�_(k��i)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ָ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ā�(l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·��(j��ng)�Ӱ�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˘O�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ָ��·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ƫҪ·�^(gu��)�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6��8�Տ����ֆ��̕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Q���T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7�յ��_(d��)�Ӱ����ë�ɖ|�ڗ��?gu��)X�й�����Y�Þ���һ�н��L(f��ng)ϴ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ϯ�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ϝh巡��m(x��)��ͤ�Ȕ�(sh��)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죬ë�ɖ|�ٴ��ڽ��H̎�O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ɺ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1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ɺ����;������ٴν�(j��ng)ͣ�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(x��)��ͤ���cȫ�̽Ӵ���11��17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(x��)��ͤ50�۳�������߅�^(q��)�����O(sh��)��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ɺ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X(j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ϝh巵���ϯ�gһ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ͥ���@�N����ů��o����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õ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ɺ�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i��n)�����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µĂ�(g��)��ʹȻ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ë�ɖ|���й��I(l��ng)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n��i)��߀��һ��(g��)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̽ҕ��ħ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(x��)��ͤ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ɺ��֪�m(x��)��ͤ�ɕx���D(zhu��n)�Ӱ��β����B(y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xi��)�Ňڸ����Ӱ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÷��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ˣ��m(x��)��ͤ�����µ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ἰ���
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�ʹ��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m(x��)��ͤ�ļ����еĕ�(sh��)�Ź����߷⣬�H������ɺ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Ō�(xi��)��1946��10��21����1947��2��22��֮�g���r(sh��)�g��ȃH4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ͬ�����}�����DŽ�(d��ng)�T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ɺ��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x�졣��1946��10��21�յ�����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ʼ�K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qԥ��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ͬ�ˣ������㮔(d��ng)�C(j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(sh��)�l(f��)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ë�����켰�������Tؓ(f��)؟(z��)�˛Q���ゃ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ܲ��{(di��o)�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w���ơ��P(gu��n)�����Ўײ������y(t��ng)һ����(l��i)�w��ָ�]����ֵ��֮�H�����(gu��)���h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Ѻ�Ȼ�Q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(d��ng)ȫ���(n��i)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�(g��)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繲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(x��)��ͤ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ɺҲ���Ӓ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2��9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ɽ���x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Ҷ��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֎׳ɏU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v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m(x��)��ֻ�м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ٌ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Ҫ��Ĵ˳Կ��繲�a(ch��n)�h�ˡ�ֻ�����̖(h��o)������Ӱ�ȫ��(gu��)�О�֮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(zh��n)�䣬Ҫ���k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M(j��n)�˾S���p��؟(z��)�y֮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̎Ҳ�������1947��Ԫ��17�գ������Ӱ��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�m(x��)��ͤ���D(zhu��n)�ƕx��;�Е��ӽ��¡��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qi��ng)�{(di��o)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�ܣ�����(l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ϯ�˴λ�(l��i)���Մ����Ć�(w��n)�}����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(l��i)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y(t��ng)һָ�]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܊������L(zh��ng)���Ա�����ֻ��һ�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(gu��)�Z(y��)Ҳ������Ҋ(ji��n)���g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\(ch��ng)Ҳ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й�����ĸ߶����κ����\(ch��ng)���Σ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m(x��)��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ɺ���I(l��ng)�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r(sh��)��̎�����ԣ��Q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ɺ����r�猍(sh��)�،�(xi��)�Ÿ��V���m(x��)��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ʾ�˛Q�����c��(n��i)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hu��)Ч���ڇ�(gu��)���h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(d��ng)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I(y��)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Ը���m(x��)��ͤ��1947��2��22�ջ���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�҂�������ֺ���ՄԒ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D(zhu��n)���Ӱ����ë�ɖ|����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ɺ��λ���F(xi��n)�ھ���Ҳֻ�������@һ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ڸ���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l��i)��?z��ng)Q�M(j��n)ֹ�����ë���쮔(d��ng)Ȼ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Ğ��y̎��(d��ng)Ȼ����Տ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ź����߀��Ԋ(sh��)���ס��Z(y��)�����L(zh��ng)����b���xđ���S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ڕ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߀֮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(x��)��ͤ��1947��9��12������11�r(sh��)��ɽ���d�h��Ȼ�L(zh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ӵ�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ɺ��ʹ�f(w��n)�֡���(zh��n)�y�o(w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ʹ�Լ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ܰю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

 ��ӡ���(y��)
��ӡ���(y��)